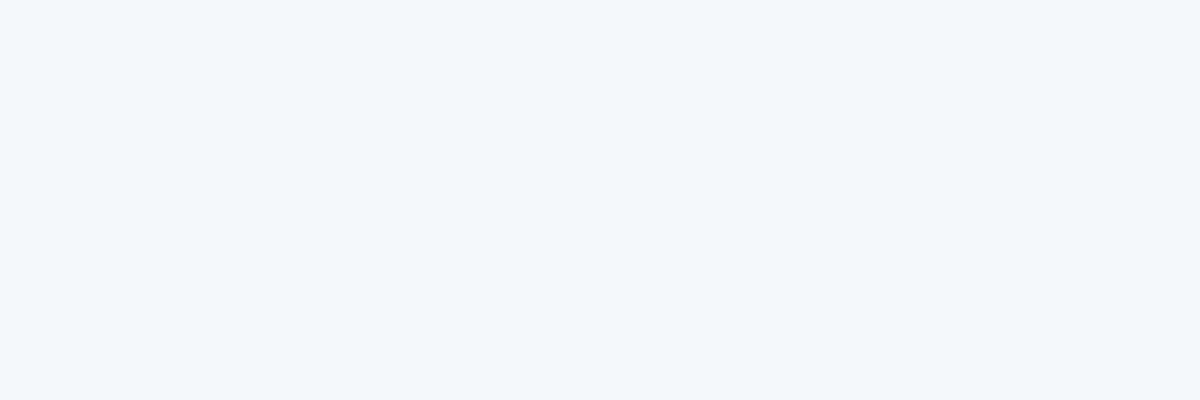原创短篇小说2000字左右
我需要一篇2000字的原创小说,交作业。
影子 很久很久以前,在寒冷的北方有一位博学的学者。他写过很多书,人们尊敬他,有不明白的事都去请教他,他也十分乐意帮助人们。 一次他应南方人民的请求南下去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地方太热了,太阳像个大火球,烤得房屋和街道都要冒烟了。学者难以忍受酷热,只有在太阳落山后才能工作。 一天晚上,学者在窗前思索。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影子站在对面房间的阳台上,似乎要进对面的屋子,他清楚是烛光送影子去的。 他第一次清楚地面对自己的影子,有些惊奇。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的影子不见了,大为惊讶,左顾右盼,却怎么也没有找到。他心里纳闷: “难道影子昨晚留在那个房间没有出来?” 当天晚上,学者站在窗前向对面阳台望去,但是影子没有出现。学者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想:没有影子,别人会议论的,认为我是个不正常的人。人们会误解我,疏远我。 学者焦急不安地等了几天,影子还是没有回来,草草解决了问题,他就回家了。人此闭门不出,埋头研究工作,几乎与社会隔绝了。人们很奇怪,都认为他遇上了什么难题,也就不再去打扰他。 一天,学者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外面站了一个模样很像自己的人,他很疑惑,问那人: “你找谁?” “你不认识我了?” 学者仔细看了看,仍然摇摇头,说: “不认识。” “我是你的影子啊!”那人说。 学者睁大了眼睛,问: “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怎么找也没找到你,怎么你会说话了?” 那人说: “我在南方时,走进你房子对面的房间里。” “那房间里有人吗?” “那里住了一位仙人,他用法术让我看到很多人们看不到的事情。很多事情的内幕我都知道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罪恶,太多的假相,我比跟着你的时候清醒多了。” 学者问道: “这次回来你还走吗?” 那人说: “我看到了太多的内幕,太多的假相,我必须把一切公诸于世,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我是影子,很多事情无法完成,我必须变成真人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学者问: “那你怎样才能变成一个真人呢?” 那人说: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请你屈尊做我的影子。因为真正的人是不能没有影子的。” 学者说: “那怎么行!你是我的影子,怎么反要我做你的影子。” 影子苦苦哀求,说得情真意切入情入理,让学者不能不答应。 于是,影子成了学者,而学者反倒成了影子的影子。 影子成了学者之后,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想伸张正义,戳穿内幕假相了。变成影子的学者对他说: “你得履行自己的职责,既然你知道那么多黑暗的事情,你就应该大胆地揭露出来。” 变成学者的影子却说: “我不能说实话,那样我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我必须保持沉默,像一个真正的学者。” 变成影子的学者叹了口气,不再言语,似乎明白了什么。
2000字的小说 原创不可以有一点抄袭 不要写的太好
大纲:一年又四个月前女主(叶晶)被男主(炙寒)告白,四个月后,炙寒挽着另一个女生(杨依依)对叶晶说分手,一年后炙寒回来,对她说其实是他患上了白血病,为了不让叶晶伤心才把他的表妹说成女朋友,然后他的病已经治愈了,再然后他俩在一起了。结尾已经写好了。实在不好意思啊。
谎言里的幸福
一天、两天、三天······己经一年了。
叶晶坐在梧桐树下微微叹了口气。仰头,是满树的枯枝黄叶。“炙寒,你还好吗?”她有些想念那个男孩了,那个即使是离开了她,也依旧会不经意想起的男孩。
一年又四个月前。
大二(三)班的教室
他抱着一大束玫瑰花,眼睛闪闪的散发着光芒“你好,我叫炙寒。叶晶,”他的嗓子因为紧张显得有些沙哑:“我喜欢你,可以和我交往吗?”叶晶愣了愣,说:“抱歉,我不能接受。”她讨厌这样的人,她知道,每天都要发生这样的事,她也知道,他们只是喜欢她的样子罢了。
叶晶刚要转身走出教室,炙寒又叫住了她。“你可以接受我的花吗?”很失望的声音。她看见那个男孩刚刚散发着光芒的眸子已经暗淡下来了,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叶晶这次是彻底愣住了。她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炙寒:一米八左右的个子,五官端正清秀,让人第一眼就觉得这是个阳光的男孩。
“我愿意。”她笑了,“是以你女朋友的身份。”炙寒猛地睁大了眼睛,声音有些颤抖:“真的吗?太好了!你答应了!”周围的人群爆发出一阵阵惊讶的声音:“不是吧,从来都不接受男生告白的叶晶竟然有男朋友了?”“炙寒运气也太好了,我的叶女神啊!!”
叶晶轻轻地挽住炙寒的胳膊
结尾:他笑着说:“对不起,我爱你。”
高分悬赏2篇短篇小说..800-2000字.要是名家的.出名的
。
躺在草地上仰望着烟火,不记得哪一天哪一个人说过。
即使不能善待,但那依旧是恩慈,只是幻觉稀薄,即使再剧烈,仍只是烟花,留下的不过一地冰冷的尘埃。
是啊,就算曾经再怎么美好也只是曾经。大家都不是那一种谁离开谁就活不下去的人,你有你的路要走,我有我的桥要过,我们只是红尘渺小的过客。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我想如果我那时候挽留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我不知道结局怎么样,我只知道我们都付不起那个结局的代价。即使贷款,我们也还不起那个利息,何况这个社会根本不允许我们这种人贷款。
引子。
我,不是同性恋,只不过爱上同是女生的你。
Chapter.01 夏至未至,邂逅。
第一次看到你,真的有传说中的心动。
因为你的狗咬了我小腿。
你说,“我的狗只咬名牌,从中说明你的裤子是名牌,是不是很高兴。”
我说,“你的狗真是有贵族气息。”
你说,“你怎么知道?挺有眼光的,不过你体育真的不行。”
那时候我对你非常心动。如果我两条腿的人类跑赢了你带有贵族血统的狗,那么明天晨报上就会有我的身影。
于是,我在卫生站打了一个月的狂犬疫苗。
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你家的小狗小乖刚生完BB,而我好死不活的撞到枪口上。
你问我,“你是不是在逃通缉犯,一定是我家小乖闻到了犯罪的气息。”
我告诉你,“你家小乖一定是得产后抑郁症了。”
Chapter.02 秋天的童话,原来是喜欢。
生活就是俗套的十二点档的狗血情节。
我和你是同校同年级。
然后互相摧残和折磨。
有一次你又来诱惑我跟你旷课私奔。
你说,“爷,你就跟小妞我私奔吧,小妞我一定好吃好喝待你。”
我严肃告诉你,“你是肾上腺激素分泌过多,还是无聊因子侵害了大脑神经末梢。”
你也很严肃的告诉我,“我看最变态的是你吧。”
然后还是很没原则的跟你逃课。
那一次逃课,你带我来了红灯区。
瞠目结舌的是,世界上有同性恋这种生物。
晚上回家后,即使喝了5大杯凉开水,也睡不着。
脑子里浮现的是你的身影。
那个时候有一种冲动,好想爬到屋顶上去唱国歌。
Chapter.03 冬至未至,禁忌之爱。
总是不自觉的想起你,很想说喜欢你。
这念头刚冒出来,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
后来,总是避开你,我躲你是因为我怕你,我怕你是因为喜欢你。可是又想接近你,忍不住追随着你的背影,忍不住偷偷看你。你知道,我是个很没原则的人。
我给自己定了个计划,想你一次就买一粒安眠药。
当我买到11粒安眠药的时候,朋友宸告诉我,他喜欢你。希望我帮他。
我答应了。
当我买到23粒安眠药的时候,你和宸在一起了。
忘不了,你微笑告诉你,“你想要这种结果,我就如你所愿。”
Chapter.04 冬至,禁止悲伤。
看到你们幸福的在一起。
想祝福你们,可是话在喉咙里发了酵。
不过是喜欢一个人,凭什么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我想要你知道我的心情。
可是老妈在晚饭的时候,聊到了同性恋。
老妈说,“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生物,真是恶心。”
原来我妈偷看了我日记。
那一次,我离家出走。
不是愤怒,是逃避。
世界真的很现实,你笑的时候它跟着你笑,你哭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在哭。
我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狠狠的哭,是啊,我真是个变态。
回到家里时,老妈还在客厅里哭,老爸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
老爸狠狠打了我一巴掌,“你还知道回来!我怎么养了个你这样的女儿!这么多年书你白读了!礼义廉耻都不知道!”
没有辩解,只是颓废的走进了卧室。
从那一天起,邻居都知道有一个同性恋。
大家用一种异样新奇的眼光看着我。
只有你,钰,你眼中没有歧视。即使我老妈闹到了你家。
眼泪滴滴答答如时间般落下。
我告诉你,“我个变态喜欢你,希望你离我远点。”
你握紧我的手,告诉我,“被你喜欢是一种幸福,我为什么要远离这种幸福?”
Chapter.05 春天华尔兹,所谓幸福。
我们就这样简单的幸福着,并没有妨碍着别人。
也许是由于太幸福,幸福到来不急失去。
你妈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来不及感受眼泪的温度。
才明白,我们不应该幸福。
一个人在家中,数着安眠药,一共有326粒。
一不小心碰掉了手边的镜子,看到了镜子里破碎的自己。
原来自己是这么恶心,恶心到吐。
狠狠地在厕所里边哭边吐,吐到舌头都麻木打结。
一粒又一粒的把安眠药含在口中。
当含到第4粒安眠药的时候,舌头才有了知觉。
原来安眠药是苦的。一颗又一颗热泪滚滚的落到地上,摔个粉碎。
只是,疑惑的是,我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安眠药,还没有睡着。又一个坑害消费者的无良商家。
Chapter.06 夏至未至,留在原地。
最后,彼此还是说了再见。
那一天在机场里面,我们玩了一句话一个字的小游戏。我还清楚的记得。
钰:今天,天气很好。
我:今。
钰:学了这么久的萨克斯,终于可以奔京城了。
我:学。
钰:小妞奔前程去了,爷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小。
钰:小妞想告诉爷一个秘密。
我:小。
钰:我一直以来喜欢的是谁?
我:我。
钰一副阴谋得逞的表情,原来爷一直都知道,所以我们会在一起的!
会在一起吗?
看着她的身影逐渐远去,这样算不算欣赏一种残酷的美。原来一切都是花自飘零水自流。
我知道,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可能飞过沧海。
结尾。
仰首,烟花正寂寞。
就算它燃烧得再怎么剧烈,落下来的还是一地冷冷的尘埃。
也许它寂寞是因为它知道未来的结局。
既然如此,又何必来次毁灭性的燃烧呢?
参考资料: 亲身经历
短篇小说,情节结局反转,出乎意料的,2000字以内
最后的常春藤叶
【美】欧 亨利。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仿佛发了狂似地,分成了许多叫做“巷子”的小胡同。这些“巷子”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一条街本身往往交叉一两回。有一次,一个艺术家发现这条街有它可贵之处。如果一个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在这条街上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时候,突然碰上一文钱也没收到,空手而回的他自己,那才有意思呢!
因此,搞艺术的人不久都到这个古色天香的格林威治村来了。他们逛来逛去,寻找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接着,他们又从六马路买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烘锅,组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珊在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屋的顶楼设立了她们的画室。“琼珊”是琼娜的昵称。两人一个是从缅因州来的;另一个的家乡是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八马路上一家“德尔蒙尼戈饭馆”里吃客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她们对于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结果便联合租下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间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蹑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但是,在这错综复杂,狭窄而苔藓遍地的“巷子”里,他的脚步却放慢了。
“肺炎先生”并不是你们所谓的扶弱济困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女人,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没有什么血色了,当然经不起那个有着红拳关,气吁吁的老家伙的常识。但他竟然打击了琼珊;她躺在那张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望着荷兰式小窗外对面砖屋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位忙碌的医生扬扬他那蓬松的灰眉毛,招呼苏艾到过道上去。
“依我看,她的病只有一成希望。”他说,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那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你的这位小姐满肚子以为自己不会好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
“绘画?——别扯淡了!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小口琴似地哼了一声说,“难道男人值得——别说啦,不,大夫;根本没有那种事。”
“那么,一定是身体虚弱的关系。”医生说,“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可是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么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我就得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要是你能使她对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发生兴趣,提出一个总是,我就可以保证,她恢复的机会准能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离去之后,苏艾到工作室里哭了一声,把一张日本纸餐巾擦得一团糟。然后,她拿起画板,吹着拉格泰姆音乐调子,昂首阔步地走进琼珊的房间。
琼珊躺在被窝里,脸朝着窗口,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苏艾以为她睡着了,赶紧停止吹口哨。
她架起画板,开始替杂志画一幅短篇小说的钢笔画插图。青年画家不得不以杂志小说的插图来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而这些小说则是青年作家为了铺平文学道路而创作的。
苏艾正为小说里的主角,一个爱达荷州的牧人,画上一条在马匹展览会里穿的漂亮的马裤和一片单眼镜,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重复了几遍。她赶紧走到床边。
琼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在计数——倒数上来。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接着是“十”、“九”;再接着是几乎连在一起的“八”和“七”。
苏艾关切地向窗外望去。有什么可数的呢?外面见到的只是一个空荡荡、阴沉沉的院子,和二十英尺外的一幛砖屋的墙壁。一标极老极老的常春藤,纠结的根已经枯萎,樊在半墙上。秋季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吹落了,只剩下几根几乎是光秃秃的藤枝依附在那堵松动残缺的砖墙上。
“怎么回事,亲爱的?”苏艾问道。
“六。”琼珊说,声音低得像是耳语,“它们现在掉得快些了。三天前差不多有一百片。数得我头昏眼花。现在可容易了。喏,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艾。”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等最后一片掉落下来,我也得去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大夫没有告诉你吗?”
“哟,我从没听到这样荒唐的话。”苏艾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数落地说,“老藤叶同你的病有什么相干?你一向很喜欢那株常春藤,得啦,你这淘气的姑娘。别发傻啦。我倒忘了,大夫今天早晨告诉你,你很快康复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好的希望是十比一!哟,那几乎跟我们在纽约搭街车或者走过一幛新房子的工地一样,碰到意外的时候很少。现在喝一点儿汤吧。让苏艾继续画图,好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给她的病孩子买点儿红葡萄酒,也买些猪排填填她自己的馋嘴。”
“你不用再买什么酒啦。”琼珊说,仍然凝视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不要喝汤。只剩四片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的藤叶飘下来。那时候我也该去了。”
“琼珊,亲爱的,”苏艾弯着身子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在我画完之前,别睁开眼睛,别瞧窗外?那些图画我明天得交。我需要光线,不然我早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珊冷冷地问道。
“我要呆在这儿,跟你在一起。”苏艾说,“而且我不喜欢你老盯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藤叶。”
“你一画完就告诉我。”琼珊闭上眼睛说,她脸色惨白,静静地躺着,活像一尊倒塌下来的塑像,“因为我要看那最后的藤叶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像一片可怜的、厌倦的藤叶,悠悠地往下飘,往下飘。”
“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我要去叫贝尔曼上来,替我做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去不了一分种。在我回来之前,千万别动。”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上的胡子,从萨蒂尔似的脑袋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是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他老是说就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了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之外,几年没有画过什么。他替“艺术区”里那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地谈着他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区狗。
苏艾在楼下那间灯光黯淡的小屋子里找到了酒气扑人的贝尔曼。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一幅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静候杰作的落笔,已经有了二十五年。她把琼珊的想法告诉了他,又说她多么担心,惟恐那个虚弱得像枯叶一般的琼 珊抓不住她同世界的微弱牵连,真会撒手去世。
老贝尔曼的充血的眼睛老是迎风流泪,他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连讽带刺地咆哮了一阵子。
“什么话!”他嚷道,“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小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艾说,“高烧烧得她疑神疑鬼,满脑袋都是希奇古怪的念头。好吗,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替我当模特儿,我也不勉强了。我认得你这个可恶的老——老贫嘴。”
“你真女人气!”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走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说了半天,愿意替你替你效劳。天哪!像琼珊小姐那样好的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啊。”
他们上楼时,琼珊已经睡着了。苏艾把窗帘拉到窗槛上,做手势让贝尔曼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他们在那儿担心地瞥着窗外的常春藤。接着,他们默默无言地对瞅了一会儿。寒雨夹着雪花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翻转过身的权弃岩石的铁锅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艾睡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看到琼珊睁着无神的眼睛,凝视着放下末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上去,我要看。”她用微弱的声音命令着。
苏艾困倦地照着做了。
可是,看哪1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片了。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那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
“那是最后的一片叶子。”琼珊说,“我以为昨夜它一定会掉落的。我听到刮风的声音。它今天会脱落的,同时我也要死了。”
“哎呀,哎呀!”苏艾把她困倦的脸凑到枕边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可怎么办呢?”
但是琼珊没有回答。一个准备走上神秘遥远的死亡道路的心灵,是全世界最寂寞、最悲哀的了。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联系一片片地脱离时,那个玄想似乎更有力地掌握了她。
那一天总算熬了过去。黄昏时,她们看到墙上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旧依附在茎上。随夜晚同来的北风的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从荷兰式的低屋檐上倾泻下来。
天色刚明的时候,狠心的琼珊又吩咐把窗帘拉上去。
那片常春藤叶仍在墙上。
琼珊躺着对它看了很久。然后她喊喊苏艾,苏艾正在煤卸炉上搅动给琼珊喝的鸡汤。
“我真是一个坏姑娘,苏艾,”琼珊说,“冥冥中有什么使那最后的一片叶子不掉下来,启示了我过去是多么邪恶。不想活下去是个罪恶。现在请你拿些汤来,再弄一点掺葡萄酒的牛奶,再——等一下;先拿一面小镜子给我,用枕头替我垫垫高,我想坐起来看你煮东西。”
一小时后,她说:
“苏艾,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不勒斯海湾写生。”
下午,医生来,他离去时,苏艾找了个借口,跑到过道上。
“好的希望有了五成。”医生抓住苏艾瘦小的、颤抖的手说,“只要好好护理,你会胜利。现在我得去楼下看看另一个病人。他姓贝尔曼——据我所知,也是搞艺术的。也是肺炎。他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病势来得很猛。他可没有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进医院,让他舒服些。”
那天下午,苏艾跑到床边,琼珊靠在那儿,心满意足地在织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户巾,苏艾连枕头把她一把抱住。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害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痉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的夜里,他窨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原来地方挪动过的样子,还有几去散落的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和了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末了——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它为什么在风中不飘不动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 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
急求2000字左右的文章
阅读。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它好“的欧亨利式的结尾”他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戏剧性的情节,铺垫,铺垫,勾勒矛盾,最后在中的字符突如其来的变化到底,这样发生的心理状况,或突然逆转,使读者感到突然,突然,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主人公的命运,不禁站在惊讶,造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欧亨利团结的灵魂在小说的结尾都是读者的前面的一部分似乎是平淡,但迷宫是诙谐的描述听起来很吸引人,不知不觉到精心设置直到最后笔者,顿时如一道闪电,它照亮了先前隐藏的一切,仿佛读者和捉迷藏,或玩障眼法,给读者最后一个惊喜。在此之前欧亨利,其他短篇小说一直这么试过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但这种使用欧亨利的更频繁,更自然,更熟练老到。
警察和带家具的房间
/>最后一个财富和常春藤的叶片<两年后的贤士手掌。
厄洛斯是一种壮阳药可能失算
精神分析的结婚一个月
艾基那岛·Sheensitan的摩天大楼。
快乐失语症患者注意到贷款票据
BR p>绝招英雄狼剪头发决斗。
优势结束大臣专业户几个侦探
千元幽静的环境路人 BR />“杀人犯”
伯爵,错过了参加婚礼的客人
非歌剧般的戏剧波折<BR 。
人们期待的巧合和Tonya红玫瑰生活p> 。
燃烧的仇恨卖面包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