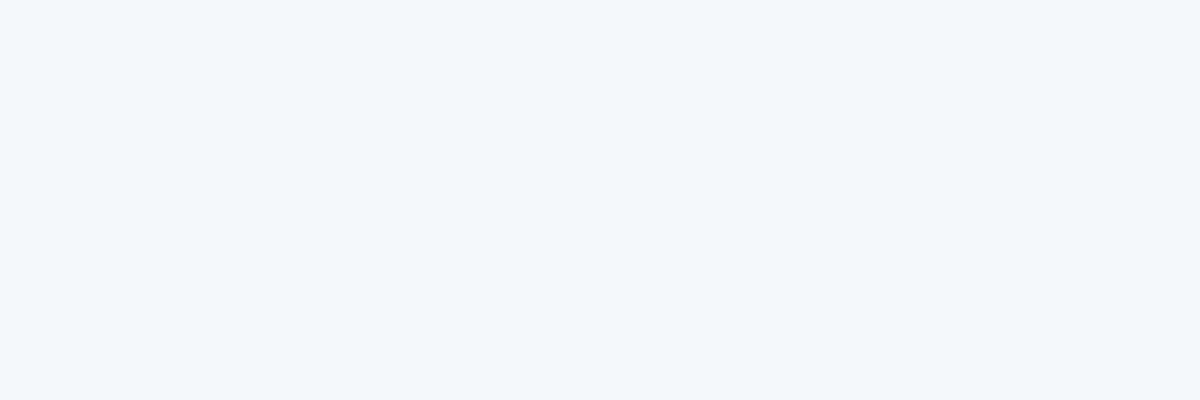最后一只猫刘亮程阅读答案
住多久才算是家 刘亮程 阅读答案
1、文章第二段中加点的词语“似乎”能不能去掉?为什么?
2、给文章第三段的空白处填上恰当的词语。
3、本文是按什么顺序来记叙的?找出相应的词语。
4、请你从上文中找出与“肯定被人打的”相应的语句。
5、“它知道它在村里干的那些事。村里人不会饶它。”中"那些事”指的是什么事情?1.不能 (原因太简单了)因为“似乎”说明并不是绝对对它失去耐心。反之,如果去掉,则没有这个效果。
2.爬 到 贴 出 扑 望。
3.时间顺序。;“又过了几个月”,“第二年”。
4.“黑猫也没再露面,我们以为它已经被人打死了”。
5.偷吃村里的鸡。
刘亮成《一个人的村庄》读后感
你好!感谢信任,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参考答案】
1、文章第二段以牛为例,意在说明什么?
以牛为例,意在说明家的珍贵印迹。牛为人做出巨大贡献,与人朝夕相处,在农人眼中是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2.第三段说“一个人活得久了,麻烦事也会多一些”,有那些麻烦事呢?请结合文本进行分析。
文中“那些麻烦事”指的是与“我”一同生活过的众多事物给“我”留下的珍贵印迹。如腰上的母牛蹄印、腿上的狗的牙印、脸上蚊虫叮咬的痕迹、身上女人留下的痕迹。
3.“我”为“自己没有离开这个村庄”一直感到庆幸,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离开村庄,也就没有离开那个生活多年的家,也就没有淡忘那些家的印迹。从而让“我”始终感受的到家的温馨与气味。饱含着对老家的眷恋和生活的热爱。
4.文章的题目为“住多久才算是家”,你认为一个地方住多久才能为家呢?请说说你的思考。
我的观点是所谓的家就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与情感的慰藉。只要你投入了情感与爱,做出过牺牲与付出,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迹,那么时间即使再短,也是家。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愿对你有所帮助!
一个人的村庄 这篇文章全文,不要是节选的,那里有?
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守望着精神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人与自然万物各适其所的和谐相依,
每个生命的存在都有其不可剥夺的合理性,
都是一个奇观,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守望着精神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人与自然万物各适其所的和谐相依,
都有一部纷繁且无法穷究的心灵
史,都保持着卓然独立的个性,因而也不能为外部世界的轻易改变。因为“其实这些活物,
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
它们没有走远,
永远和人呆在一起,
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
自己”
,所以“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
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
。他写了“狗这一辈子”
、
“逃跑的马”
、
“最后一只猫”
、
“两窝蚂
蚁”
,也写了“一条土路”
、
“我认识的那根木头”
、
“野地里的麦子”和“一截土墙”
,因为它
们和黄沙梁的村民共同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故乡的意义,
在他的心中,
始终有两层含义:
一是生存之地,二是精神居所。作家曾如此说过:
“故乡对中国汉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我们没有宗教,故乡便成为心灵最后的归宿。
”
他安详、
贪婪地感受和享受着家园带给他的幸福和满足,
家园永远是那心灵的栖居地,
哪怕
是破败的草屋荒芜的庭园也是心灵憩息的地方。
在不断地迁徙,
不停地漂泊中,
我们在何处
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也许《一个人的村庄》是个很好的去处。
我们知道世上有如此多的虫子,
给它们一一起名,
分科分类。
而虫子知道我们吗?这些小虫
知道世上有刘亮程这条大虫吗?有些虫朝生暮死,
有些仅有几个月或几天的短暂生命,
几乎
来不及干什么便匆匆离去。没时间盖房子,创造文化和艺术。没时间为自己和别人去着想。
生命简洁到只剩下快乐。
我们这些聪明的大生命却在漫长岁月中寻找痛苦和烦恼。
一个听烦
市嚣的人,
躺在田野上听听虫鸣该是多么幸福。
大地的音乐会永无休止。
而有谁知道这些永
恒之音中的每个音符是多么仓促和短暂。
“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灵者,
以五百岁为春,
五百岁为秋;
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的《秋水》
寒蝉和灰雀这两个小东西懂得什么!
小聪明赶不上大智慧,
寿命短比不上寿命长。
怎么知道
是这样的呢?清晨的菌类不会懂得什么是晦朔,寒蝉也不会懂得什么是春秋,这就是短寿。
楚国南边有叫冥灵的大龟,它把五百年当作春,把五百年当作秋;
上古有叫大椿的古树,它
把八千年当作春,
把八千年当作秋,
这就是长寿。
可是彭祖到如今还是以年寿长久而闻名于。
世,人们与他攀比,岂不可悲可叹吗?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这是上古最智慧的人发的精辟言论,刘亮程给。
这些小虫一下子翻案了,
而且说的极为在理,
只此一段,
就值得为刘亮程的文字与哲思叫好。
记得那一年在野地,
我把干草垛起来,
我站在风中,
更远的风里一大群马,
石头一样静立着,
一动不动。
它们不看我,
马头朝南,
齐望着我看不到的一个远处。
根本没在意我这个割草人
的存在。
我停住手中的活,
那样长久羡慕地看着它们,
身体中突然产生一股前所未有的激情。
我想嘶,
想奔,想把双手落到地上,撒着欢子跑到马群中去,昂起头,看看马眼中的明天和远方。我。
感到我的喉管里埋着一千匹马的嘶鸣,四肢涌动着一万只马蹄的奔腾声。而我只是低下头,
轻轻叹息了一声。
我站在风中,更远的风里一大群马,石头一样静立着,一动不动。它们不看我,马头朝南,
齐望着我看不到的一个远处。根本没在意我这个割草人的存在。——《逃跑的马》
你读着读者就会被感染,
也和刘亮程一样,
像一个愚拙的割草人,
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但是你的心中早已抑制不住的激动与澎湃,
恨不得也变成那一群马中的一个,
随着它们一起
向远方奔跑,
或者,你已经不用真的去奔跑了,在表面看似宁静安逸的字里行间,你早已。
经随着心中的思绪飘飞到无止尽的远方了。
所以说懂得这种意境旨趣的人,
他不必周游世界,
甚至于不想去周游世界,
他却已经绕着每一个国度走了很远了,
这大概就是阅读的乐趣之一
吧。
一个人的村庄
饱含着清新土香的味道,充满大自然的气息,来自纯朴乡村的点滴,人或物都散发着野性的自然,毫无做作,这是《一个人的村庄》留下的足迹,挥发了一切现实的复杂与繁琐。他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有人称之为“乡村哲学家。林贤治在《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中满腔感性地说:“这是狂哞,是撕心裂肺的声音。惊恐、愤怒、决绝,整个文坛听不到这种声音。没有一个来自乡土的作家能够如此看待自己的出身、处境和命运。”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村庄》的字里行间隐隐地透露着作者对黄沙梁生活一种泰然处之的态度,在平素无波澜的文字里深藏着深刻的生活哲理,鞭辟入里,不免给读者心里留下一笔深深地隐形痕迹。
应该说刘亮程这位乡村哲学家在逃避着现实生活;还是在他的眼底里,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农民生活真的名不虚传,有如他散文笔下的淳朴之美?。
一个人畜共居的村庄,留在这里忙着生活的村民,替人干农活的铁锹、锄头、镰刀,在田野中摇曳的草木,在风中浅唱的虫兽,归属于这块土地的作者——一切人和物,就这样与乡野的孤陋和粗鄙依傍着,与激情野性的牲畜共居“一室”。在这个落后的村庄里头,有只得呆在村庄老死的狗,在自己认定的命运里逃跑的马,与驴性互通的人,在深夜里与己伴眠的小虫子,花花草草,人畜共处……黄沙梁上扬起的尘土,锄头和铁锹轻碰的声音,牲畜勤勤恳恳的一生,穿过门窗肆虐的风,烟囱上少遇的袅袅炊饭味,为了一把镰刀和一捆青草苦苦找寻了一辈子的我。在刘亮程的笔下,没有绝望的渴求,即便在平白旷远的文字里倾注着对村庄周围里外的深沉哀叹,也时不时地在简单中酝酿出不平凡的哲理,这是对一种命运的豁达,对生活的高深理解与个人的淡然,挖掘着在不同的牲畜身上演绎的一生:
1、在《狗这一辈子》里面,似乎狗终其一生,都只是这个样子,在人的面前,或在门口晃荡着,然后随着时间成为陈年旧影中的一点。作者说:“……这时的狗很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世界已拿它没有办法,只好撒手,交给时间和命;”“狗这一辈子像梦一样飘忽,没人知道狗是带着什么使命来到世上。”想来,要成为一条又忠实又能活到老的狗实属不易,在村庄寂静的夜里,才有着狗自个的世界。而人能在狗的眼中看到往日的身影,人和狗也都是即将沦为历史尘埃的一份子,从出生开始,并不知道生来何惧,在一段属于自己的旅途上溜达,做着分内事,平平凡凡地活一辈子。
2、抑或,像一直往前狂奔的逃马,驮着人飞奔到早已注定生死的路口,人不也只求摆脱一切宿命的安排?而人的命运,或许正如作者所说的:“也许人的逃生之路正是马的奔死之途,也许马生还时人已经死归。”马逃跑纯粹是为了自己,在“马并不是被人鞭催着在跑,不是。马在自己奔逃。马一生下来便开始了奔逃。人只是在借助马的速度摆脱人命中的厄运。”这句原文当中,我突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在刘亮程眼中的马,它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微妙的世界。
——“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来自《剩下的事情》) 诠释永恒,那是作者看待生还和死归的一种坦然心态。作者巧妙地用了“安静的哲学”来彩绘这幅“村庄素描图”,美化这个平凡的家园,使它成为了一个寄托精神和安定生活的圣地,与人畜共享这块净土的安谧、祥和,从而在精神的食粮中获取温饱。黄沙梁不是刘亮程笔下荒芜的乡野,它实际是每个人心底最温柔的家园。返濮归真的农村生活是他勾勒每一个平等存在的人或物的原料,“一是生存之地,二是精神居所”是刘亮程心中赋予黄沙梁的定义。在刘亮程的这部散文集里,不难看出文辞间隐隐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气息,比如《狗这一辈子》、《寒风吹彻》、《冯四》、《有人死了》、《家园荒芜》等篇章中,这里边传达了作者在黄沙梁积淀几十年的深厚感受,一种对精神家园难以割舍的情愫:那里有他挚爱的妻子芥,苦苦等待着不知归途的人儿的记忆;那里有让他得以呼吸的风,可以徜徉野草树木;那里有一起拓荒的纯朴村民;还有一切大大小小的牲畜虫蚁……这些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人或物,它都是“精神家园”里的主人,各自为自己无知的未来,难测的命运倔强地奔波着。
这本书,像再次卷起了黄沙梁上厚厚的黄土,而扬起的尘埃飞扑到人们的脸庞上,使人直视它的桀骜那刻,也慢慢通过雨水渗透肌肤的冰凉感受到平凡生命的叛逆,在假设生与死注定的结局里,看着身边每一样事物活过一辈子的姿态,在眼底下暗自判断着他们存在的价值与精神归宿。——《一个人村庄》充分利用了所有来自乡野村庄的点点滴滴来营造自己心里憧憬的那个“精神家园”,丝毫不放过任何可以体会农民平凡生活的因素,把虫、风、土、砖块、人、牲畜、乡情、思念、记忆……这些东西组合成一个具有意象诗意美又不失朴素纯正的“精神故乡”。
一把生了锈的钥匙,几块为了藏钥匙的土砖,在这“一个人的村庄”里,他在挨月挨年地等着自己的妻子,带着仅存着的记忆,在孤独的荒野上,在空荡的院子里,在没有温度的炕上,在没有炊烟的厨房……看了《一个人的村庄(节选)》,我惊奇的发现,在这个村庄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勾起作者对妻子芥深情款款的回忆,难以释怀的眷恋,沉淀在黄土里的呼喊,无期限的等待和不间断的低喃成为了他在黄沙梁日趋刻骨铭心的精神支柱。看着周围的人走完他的一辈子,然后告别熟悉的这块土地,但始终停留不走的那个梦里都塞满了荒芜家园的影像。我看到,作者在用他那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在撕心裂肺呼喊,直到嘶哑疼痛的喉间叫不出半个字儿。活了大半辈子,眼中都早已填满了生命的归途,这是刘亮程笔下的村庄,写满了乡野生活最普通的事物,却无一不可从中品茗到其中的哲思,诙谐中带着微妙肌理,自然中含着抒情哲理。这是一部勾勒乡野的田园画,简单中不失淡雅,一词一句中夹杂着深晦的价值观,这也是构建这座精神家园的根本材料。
冯牧文学奖评委会给予了这本书高度的评价:“刘亮程的写作延续着中国悠久灿烂的散文传统。他单纯而丰饶的生命体验来自村庄和田野,以中国农民在苍茫大地上的生死衰荣,庄严地揭示了民族生活中素朴的真理,在对日常岁月的诗意感悟中通向 '人的本来'。他的语言素淡、明澈,充满欣悦感和表达事物的微妙肌理,展现了汉语所独具的纯真与瑰丽。”
慢慢斟酌《一个人的村庄》,可以意会到文中不断渗透出来的奥妙真理,在人和牲畜共居的家园里,在风中的家园里,抑或在荒芜的家园里,这都是一个人的村庄里的真实写照。作者在挖掘着这个“精神家园”,改变着里边事物的同时,也是在改变着自己的世界,使自己在荒芜的家园里诗意地生活着。刘亮程在自己的散文中传达的是一种单纯质朴的农村生活,但是,他成功地在其间孕育了一个精神得以归属的地方。对现实凄苦生活的吼叫与哀叹,他把它转化成了对生活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思考——这一点是刘亮程文风的闪烁点,即使是一条狗,一只猫,一头驴,一阵风,一个长梦,一顿晚饭……这些事或物,都能在他的笔下独立成篇,本着那透彻心境的辟理,有意无意地刺激着读者如狂澜般的情绪,让人看透这种荒凉中的诗意,宁静中的嘶吼,平和中的高吭。刘亮程所感悟到的这种生活体验,像在苦苦地追寻着在黄沙梁里那弥漫黄土中的一点希望,而这点希望在辗转间成了他笔下的璀璨星光。品味着这无比纯净的金琼玉液,在看着刘亮程文中不断解读的生命与归宿小道理时,我们似乎会觉得他在阐释着乡野间的每一样事物的真实心绪,他是一个“能正确读懂这个村庄的所有物在想什么”的哲学家。这就是生活,在教授人适应它之余,也在被人用着自己的个人观点去诠释它。只要精神不灭,脱离肉身的魂魄就会有归属于家园的一天。黄沙梁——一位乡野哲学家的精神故园,一个积淀着他深厚感情和人世记忆的地方:(摘录)。
“我在地上只有一个行将废失的家园。在天上我没有自己的一砖一瓦。我注定要四处漂流的魂魄只有你——黄沙梁,这是唯一的去处和归宿。
当我死去,我已经全部地归属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