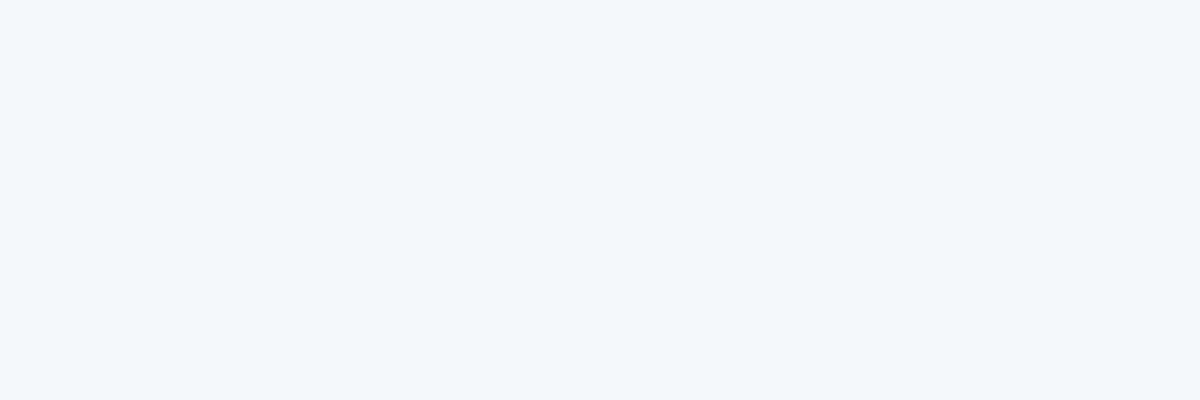王小波写性的段落
黄金时代中性的描写
对于王小波的评价,从来都是充满争议的。有人说如果王小波还在世的话,他会比莫言更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有人认为王小波的作品,不过是部黄色小说。
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小波的作品,影响了无数人。记得以前读大学时,总会到图书馆找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对于涉及未深的学生来说,书中的内容充满了诱惑。
对于性的看法,王小波是直白的。在给《性社会学》一书写的书评中写道:事实上性在中国人生活里也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享受性生活的态度和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方面没必要装神弄鬼。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宠儿
1952年,王小波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他出生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男孩中排行老二,而《黄金时代》的主人公叫做王二,不知道是不是王小波的真实写照。
王小波曾经说过,黄金时代是他的宠儿。也许是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前前后后,用了20年的时间才写成。
在许倬云的力荐之下,获得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台湾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获得一笔25万的巨额奖金,这让他决定辞去讲师的工作,成了一名作家。
可是这本书并没有因为获奖,而大放异彩。反而在港台出版后,被贴上了黄色小说的标签,甚至还被改名为《王二风流史》,而在内地,连出版都成了问题。王小波询问原因,出版社给出的回答是:小说很精彩,但现在不敢发。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文中充斥着大量直白的性描写,直到当时的华夏出版社的部门主任赵洁平,不忍心这么一部好作品,不能出版。趁着总编辑外出期间,终于让《黄金时代》正式出版。
《黄金时代》性描写到底有多直白?
那么黄金时代,到底讲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这可以说是一部爱情故事,但跟别人隐晦的爱情不同,主人公的爱情简单粗暴。
在《黄金时代》里有着铺天盖地的性描写。有人统计了下,和性相关的词语、行为总共出现不下百个,还有好几处直白的性描写——王小波把它称之“敦一敦我们伟大的友谊”。
故事发生在王二下放云南的日子里,那年,王二21岁时,腰伤难忍,找到美女医生陈清扬看腰病。半个小时后以后陈清扬下来找他,跟她讨论自己被人说成破鞋一事。
王二开始了他伟大友谊的论述,希望两人可以“敦一敦我们伟大的友谊”。两人就这样一来二去,搞了很多次。后来,陈清扬还陪着王二在僻静的山上住了半年多。
直到被领导发现,然后下山接受各种批斗。随后,各自散去。二十年后,他们重逢,再一次“敦起了伟大友谊”。从此,王二再没有见过她。
在《黄金时代》中不乏精彩直白的性描写,比如陈清扬被认定是破鞋的理由:
“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但你脸不黑且白,乳房不下垂且高耸,所以自然被认为是破鞋。”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就要证明自己的贞洁。而这对于已婚妇女陈清扬而言,是做不到的。于是,她选择成为真正的破鞋。这时反倒周围的人,便不再认为她是破鞋。
这无疑体现出人性的矛盾与露骨,也许对于周围的人来说,陈清扬是不是破鞋并不重要,他们只是想看到陈清扬出丑。可他们没想到,陈清扬选择最直白的方式来对付人性。证明不了自己不是破鞋,那就成为真正的破鞋。
对于《黄金时代》,直白的性描写,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但也让引起了很多争议。王小波和众多文人一样,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备受推崇。
高晓松多次在节目中流露出对王小波的崇拜,他说:
“以我有限的阅读量,王小波在我读过的白话文作家中绝对排第一,并且甩开第二名非常远,他在我心里是神一般的存在。”
冯唐,他说:
王小波作品的好处首先是有趣味。小波的文字,仿佛钻石着光,春花带露,灿烂无比,蛊惑人心。
李银河:小波是诗人,走得也像诗人。
如今很多人陷入迷茫之中,不如重读一回王小波。在这个繁杂世界中,也能拥有有趣灵魂的能力!推荐给大家超值的《时代三部曲》,里面包括王小波生前出版的所有小说:《黄金时代》《黑铁时代》《白银时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链接看看!
文学作品中关于性的描写
即便没有看过《黄金时代》的人,也会对其中大量的“性描写”略有耳闻:直白裸露的文字描写,有时还会让毫无心理准备的读者羞红了脸。
这也导致,《黄金时代》始终在文坛存在两极分化的评价:
有人急匆匆为它贴上黄色小说的标签;也有人惊叹它足以枪毙了所有写性的小说。
所有的认知差异,都源于最本质问题的概念模糊。
所以,人们对《黄金时代》的偏见或推崇,归根到底是为了弄清其存在意义:
王小波为什么在《黄金时代》中,展现了大量的“性描写”?
当然,弄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并非会让你完全爱上这本饱受争议的书籍,而是无论你喜不喜欢,都是真正看懂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独特之处,无疑是挣脱了时代环境的桎梏;在谈性色变的保守年代,王小波如顽童般偏反其道而行,以铺天盖地的性爱描写,惊醒了昏昏欲睡的世道和文坛。
那些对人类情欲的描写,更是精彩直白、酣畅淋漓,以至于让人胆战心惊,又欲罢不能!
更可贵的是,不管是人体结构还是欢愉场景,王小波的笔调始终是冷静自然的,将“性爱”两字掌控在不越香艳禁区中。
除了表面宣扬人们正视原始自然的情欲外,王小波更是为被权力束缚的人性自由呐喊!
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组织和指令大于一切,也如同枷锁禁锢着人性的自由。
即便当两人发生亲密的肉体关系时,权力也左右着每个人对性的想法和渴望。
【文人笔下的“性”】
文学作品中关于性的描写如下:
中国的纯文学作品,关于性描述着笔最多的现象当数上世纪九十年代了,从陈忠实到莫言,贾平凹,一个赛着一个,到王小波身上,完全活脱脱的性解放,他们的作品一亮相,着实让萎靡的现代文学雄壮了那么一瞬间。
性,这个曾经让国人羞提的话题,在文学上一下子骄傲地抬了回头。
抛开地下通俗纯色情小说不说,自《金瓶梅》后,妥妥的文化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违者简直是稀有动物,他们几位的表现还真是勇敢,而且幸运过关,在骂声与赞扬声中奠定了文坛地位,很是上那些同仁羡慕了一阵。
说实话,读过《白鹿原》、《丰乳肥臀》、《废都》、《黄金时代》的读者都明白,除了王小波的特立独行外其他几部著作就算没有性的描写,也不影响作品的完整,这也是他们被人诟病的地方。
王小波是个另类,更多的是个人精神的诠释,好似一种另类的写实,不那样写,他不好表达他对明里道貌昂然而暗里天天进行的虚伪行为的鄙视,他的文字以小见大,和大框架史诗笔法不同。
我们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总是超出作者意识,这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当出现不朽之作,他们会显现出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和沽名钓誉无啥区别。
举例《红楼梦》,简直成了一帮文人的金饭碗,那帮人用着各种意淫去挣着观众的银子,最后大伙猛然醒悟,怎么不见其个人的独立之物,全在蚂蚁搬巢,于是神坛轰然坍塌,但人家达到了目的,生活很享受。所以做读者,还是要培养智慧,不要将垃圾当宝贝还执迷不悟。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性描写?
【文人笔下的“性”】
。
作家们都怎么写“性”?
文人都怎么性?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第一个请出来的人物,是李白。
李白写性,只是写场景,而且非常讲究意境。在《寄远》中,他写男欢女爱,只写了一句“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在《对酒》中,他写“玳瑁宴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一点都不色&情,还给人以美感。
白居易写性,也比较意识流,似是而非。比如,在《花非花》里,他写:“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他只是写了对方的行踪似真似幻,似虚似实。你若是不仔细读,根本不知道他就是在写性。
相比之下,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他写性,总给人以低俗之感,像是“女乃色变声颤,钗垂髻乱,漫眼而横波入鬓,梳低而半月临肩”这种程度,算是轻的。怨不得出名的是白居易,而不是他,两兄弟写诗的情趣真是天差地别。
说到性,就不得不提兰陵笑笑生。他写的《金瓶梅》,曾一度因为写性的笔墨太多被禁。书中某些描写,堪称A片,实在是“少儿不宜”。
如果不是《金瓶梅》抛砖在前,恐怕是显不出《红楼梦》的伟大。
曹雪芹也写性,有的粗俗,有的细腻;有的直接写,有的隐写。
在《红楼梦》一书中,他会借薛幡之口说“一根J8往里戳”,也间接地暗示了香菱嫁给他之后,会被当成什么。
他写王熙凤和贾琏大中午地在家里ML,只是隐晦地写门口的丫鬟连忙摆手、奶妈含笑摇头、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人舀水。
写贾琏要找平儿寻欢,平儿怕被凤姐为难,急忙躲。曹雪芹写到这一处,来了一句“急得贾琏弯着腰恨道……”
贾琏为什么弯着腰啊?因为裤子支帐篷了,不弯腰多不体面。
这些年,有一些观点称《金瓶梅》比《红楼梦》伟大,这我是万万无法苟同的。《金瓶梅》重在揭露,对人性的刻画是赤裸裸的,而《红楼梦》重在救赎,整本书里杂糅了大量的美、爱、尊重、自由和幻灭。
《金瓶梅》若不是靠写性赚足了眼球,人们可能很难发现有这么一本书,而《红楼梦》,即使书中不费笔墨写“性”,它也能闪耀千秋。
现代作家写性,最萌的恐怕还是老舍。
在《骆驼祥子》里,他写祥子和虎妞初次交欢,是这么描写的:
“屋里灭了灯。天上很黑。不时有一两个星刺入了银河,或滑进黑暗中,带着发红或发白的光尾,轻飘的或硬挺的,直坠或横扫着,有时也点动着,颤抖着,给天上一些光热的动荡,给黑暗一些闪烁的爆裂。有时一两颗星,有时好几个星,同时飞落,使静寂的秋空微颤,使万星一时迷乱起来。
有时一个单独的巨星横刺入天角,光尾极长,放射着星花;红,渐黄;在最后的挺进,忽然狂跃似的把天角照白了一条,好像刺开万重的黑暗,透进并逗留一些乳白的光。余光散尽,黑暗似晃动了几下,又包合起来,静静懒懒的群星又复了原位,在秋风上微笑。地上飞着些寻求情侣的秋萤,也作着星样的游戏。”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写星际穿越。
鲁迅也写性,但写得极为隐晦。他写祥林嫂被强迫,只是用对话来写,祥林嫂说对方力气太大,听的人根本不信……如此而已。
在日记里,他多次提及“濯足”,有人考证说,其实他就是在用这个词来代指性生活。
郁达夫也写性,但他不直接写性场面,他写得更多的是性心理。比如说,哪次自己控制不住兽欲去找了妓,事后陷入自责、苦闷之中。
民国时代,连女性解放双足、剪头发都要大受批判,文人们大张旗鼓去写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就连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张恨水写性,也不过就是四个字:一宿无话。
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就更加没人写性了。改革开放后,文学也迎来了春天,一大堆作家像是被压抑久了,忽然大张旗鼓去写性。
贾平凹写性,非常直接,能看得你面红耳赤。他那本《废都》,换今天可能是怎么着都出版不了了,写再多“此处省略X字”也没用。
陈忠实写到性时,奶子、胸脯齐飞,文字里蓬勃而出的净是男性荷尔蒙气息,很像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小黄文。所不同的是,陈忠实写的性,能体现人物性格,而小黄文纯为写性而写性。
王小波写性,也是很直白的,但总能给人以一种荒诞感。那种只有在梦境里才会发生的,几乎完全与现实不符的荒诞感。他形容男人的身体,用词也很令人惊异:“躺在这两个腋窝中间,好像太阳穴上扣上了两个铝制水勺。”
莫言也写性,他也不直接写,而是强调的是性爱过程中的嗅觉、味觉和触觉。比如说,写亲吻,他会把女人的舌头形容为海螺肉。《丰乳肥臀》里,他写“身上蓬勃如毛的野草味道和清凉如水的月光味道”。描写一个女主角的身材,他写她“沉甸甸的乳房宛若两座坟墓”,而这个形容其实并不新鲜,郭沫若在诗里早用过类似的比喻。
有一次,莫言受邀讲解《我小说中的原型》,现场一中学生大胆提问,老师让我们读您,可您的小说中很多男女那些事,还读吗?全场哗然。莫言回答也很直接,你们最好现在别读,长大结了婚再读。
余华早期写性,也很隐晦。到了《兄弟》里,却忽然豪放了起来。李光头乱搞的那些情节,写得真是让人瞠目惊舌。
顾城写性,就像在写诗。在《英儿》一书中,他写到说英儿“野合”是这么写的:“轻轻触及了之后,就旺盛起来,胀得旺盛起来,像所有树木一样,那时我的心那么静默,我看着她起伏,如同海水。”
阿来在《尘埃落定》里写性,是高度隐喻化的,比如这句:“她一勾腿,野兽的嘴巴立即把我吞没了。我进到了一片明亮的黑暗中间。我发疯似的想在里面寻找什么东西。”
武侠小说作家写性,各有各的风格,有网友总结如下:黄易“虎躯一震”,金庸“心中一荡”,古龙“嘤咛一声”,梁羽生则是“生命的大和谐”。
写《寻秦记》和《大唐双龙传》的黄易,是写小黄文的鼻祖,不大段删除估计他的书都出版不了。金庸写性,写得非常克制,书里头的男女主角亲亲嘴唇就算大尺度了。古龙写性,给人以一种香艳感(但不露骨)。最后意思的是梁羽生,每次结尾几乎都是“生命的大和谐”。
比如,他把手一招,将灯灭了,在黑暗中,两人获得了生命的大和谐(出自《龙虎斗京华》)。又比如,在黑暗中,不,是在他们幻想中的色彩绚烂的世界里:他们获得了生命的大和谐(出自《广陵剑》)。
总之,梁羽生笔下的男女主角,就没有不和谐的。
男作家写性,大多是男性视角,只能将女性视为客体。
也有一些男性作家,尝试着代入女性的角色去写性。
苏童写《妻妾成群》,写到了女主角颂莲的性体验——“仿佛从高处往一个黑暗深谷坠落,疼痛、晕眩伴随着轻松的感觉”。
写性,最让女人感觉到舒适的,是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如触电一般”,是他对女性感受的想象。他用“女人漂浮在丰饶的大海上,男人却不断在萎缩,变得像个死人”来形容一场性事结束后男女双方的表现,倒是很妥帖。
男性作家写性,很难有写得合女性意的,甚至有一些描写,让女性读来是觉得挺不适,甚至会有一种被冒犯感。
比如李敖,有时候他写起性来,简直就是低俗。像“j8”“X 屁股”之类的词,层出不穷。不知道的,哪会联想到他是个文化人,可能只会认为他是刚从哪个窑子里出来的嫖客。
洪晃说她多年前咬牙看完余华的《兄弟》的第一章,说余华把男人想偷看一眼女人的大白屁股写绝了,但是作为女人,这段文字看得她真是太难受了。
男尊女卑社会太漫长了。长期以来,女性只是作为性客体而存在的,以至于表现在文学上,敢公然表达性体验的女性也不很多(也跟女性整体话语权不多有关)。
这就跟拍情&色片似的,几乎清一色的男性视觉,女性的身体、声音、气息等等都像是为了满足男性审美和快感而存在,就没几部是拍给女人看的。
女性作家也写性,鼻祖是李清照。很多自媒体文章,如今说起她来,都说她写艳词。可实际上,她不过就是描述了一点小女儿情态,离“艳词”二字相差甚远。像“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也不过就是挑逗而已。
到了现代,女作家写性,则开始变得大胆了起来,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用身体写作的女作者,但她们似乎就真的是纯为博取关注而写性了。
女作家中写性,写得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还是张爱玲。
早期张爱玲,在小说中几乎从不写性,到了《小团圆》,却忽然大胆了起来。写《小团圆》时,张爱玲已在美国居住多年,那时她都五十多岁了,估计也没啥可顾忌的了。
在《小团圆》里,她写过几次女主角盛九莉与邵之雍的交合。
有一句是:“忽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在坐下鞭打她,她无法相信——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抱着绒布的警棍”。
呵,成年人都看得懂,这是女主角坐在男主角身上发生的事儿。
还有一段是这样:
他忽然退出,爬到脚头去。“嗳,你在做什麼?”她恐惧的笑著问。他的头发拂在她大腿上,毛毵毵的不知道什麼野兽的头。
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泊泊的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著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的啜著她的核心。
这个,成年人也一看就懂。
《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我们甚至可以确定她笔下的邵之雍就是胡兰成。
我也是看完了《小团圆》,才明白了张爱玲为何曾对渣男胡兰成念念不忘。虽然花心、鸡贼了点,但人帅、嘴甜、好说话、活儿好,在床上愿意取悦女性……
在一个女人的情欲刚被开发出来的那几年,这样的男人的确让女人很难放下吧?
经典文学中的性,更多只是作者描述人物性格、勾勒人物情感走向、描述人物思想变化历程的一种工具之一,它可能事关欲望与道德、天性与束缚、灵与肉的冲突等等,体现的是作者对社会、对人性、对道德、对两性关系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但是,真要把它给写好,其实也非常不容易。
你写两个人谈恋爱,可以掰扯出好几万字来,但真要把“性”给写好,非常考验功力。而一个作家功力的深浅,可能也就在那短短的几百字描述里,可以看得出一二了吧?
。
丁俊贵
2019年1月14日
王小波的小说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幻想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时代三部曲”是由三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至于故事背景则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事实上,王小波最过人之处,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并变换多种视角。表达手法方面,他擅于用江洋恣肆的笔触描绘男欢女爱,言说爱情的动人美丽场景及势不可挡的威力。其成名作《黄金时代》,文学界的评誉甚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辑白桦更说:“《黄金时代》把以前所有写性小说全枪毙了!”
他的小说其实一直不大被出版社接受,也是因为文章中的性描写。其实这些文字不如贾平凹等人的小脚文学来的露骨,也不如其它人如莫言写的一样媚俗,只是比较直率罢了。在新时期文学领域中,性禁忌依然存在,这原因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伦理价值等一些更深的层面。
抛开以上热点不谈,从没有看到有人用这样的笔法写作。在王的小说中,你可以看到,历来文学所谓真实性的规则全都被从容跨越了,他用了不同的修辞方式来写小说,大量的即兴发挥、错位的角色语体,寓庄于谐,寓文雅于粗野。读者可以在其中感受澎湃的想象力。